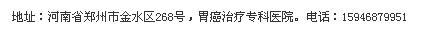但法医解释,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梁军如果是被炸而死,肺腔会产生水性肺气肿,胃部会有因窒息而产生的积液。法医还说通过对支气管的解剖,梁军死亡的时间应该和水房爆炸的时间相吻合。那就有意思了,梁军不可能在死后对田耕施暴,可法医又给出权威的解释,射精和膝跳反射一样都是脊髓的反射动作,理论上是不需要大脑参与的,死亡后的几分钟,只要性器官受到一定强度的刺激,脊髓神经一样会触发射精。法医谦虚地搓搓手,说这些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案子没了结,局里上报省厅,由卞江暂时接替这个专案小组,我依然没能逃脱掉,干的还是监控的活。可卞江没有为难我,只派给我一个任务,好好和田耕相处,观察她,了解她,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他汇报,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卞江警校毕业,破过很多大案,同事背后评价他,为人温和谦逊,但手里始终像揣着一把刀,一旦闪电般的捅向对手,一剑封喉。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木偶,无法摆脱别人对我的控制,心里憋得难受,可又无法倾诉,毕竟我有错在先。几天后的傍晚,我去田耕家里,刚要敲门,听见里面一个男人沉沉的声音,田耕,你容我好好想一想,我尊重你的意见,我不声张,也许这需要一辈子的时间。
我踮起脚跟,透过毛玻璃的窗影,里面的灯光很亮,吴晓岩拨拉着田耕的头发,田耕的身体有了反应,脸上迸出幸福的笑容,而吴晓岩低垂着头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像一条锯齿锋利地锯着我的心脏,我的心脏简直要被撕裂,我无法忍受,看到爆炸这样的场景。
听到这些话,我提不起神,我本来就不愿意卷入这件马蜂窝一样的案件里,所以有气无力地再次迈起腿,可腿一软,嗵的一声,身体意外摔倒在石台阶上。吴晓岩拉开门,愣怔了一下,一把把我拉进屋里。还算有点收获,吴晓岩向我揭开一个谜底,他的眼睛使劲盯着我,依然神情紧张,喃喃地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心里像有把刀搅来搅去,太难受了。
我懒洋洋地戏谑他,你还像个大丈夫吗?
田耕面露笑意,吴晓岩叹口气,道出水房被炸的缘故:
我离开水房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最初吴晓岩其实喘着粗气,背着一麻袋面粉偷偷摸进了门。吊扇在我头顶上呼呼吹着,他关紧水房的所有门窗,打开面粉袋,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洒满了面粉。吴晓岩表情僵硬,冲我笑的有些吃力,说面粉被吹得四处飞扬,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空气里的面粉和空气充分地混合,达到了一定的浓度。我哦了一声,那又怎么样呢?我歪着脑袋反问。吴晓岩有些莫名的紧张,问我离开水房的时候,是否看到过道里有一团黑影?我摇摇头,吴晓岩舔一舔干燥的嘴唇,僵硬的兀自微笑着说,我背着那团黑影进了水房,然后给那团黑影松绑,我点燃了打火机,瞬间关上了水房的门,就这么简单,所有的录像监控设备顷刻化为灰烬。当我远离水房,望着爆炸的火光,我那种好奇拧紧了我身上所有的神经,竟让我感觉到一种近似残酷的快感。我在空旷荒凉的地方站了足足几分钟。
现在他们在找我吗?吴晓岩问我。
我的心怦怦跳着,下意识地点点头。
那你呆在这儿干什么?田耕努力地维护着声音里摇摇欲坠的平静,她示意着吴晓岩,因为我的存在,吴晓岩有些惊慌失措,连连摇头。
不行,我不能帮助你走这条绝路,吴晓岩的语调有一种异样的苏醒和绝望,田耕捂着胸口狠狠踹了吴晓岩一脚,我这才看清田耕脸色发青,眉头紧蹙,大口喘着粗气,表情十分痛苦。
吴晓岩说,你别吓唬我,田耕。
田耕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欲哭无泪地说,你离开我什么都好了。
吴晓岩俯身想把她扶起来,田耕很重,闭着眼睛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动,胳膊无力的垂下去。还是我来吧,我将田耕扶到床上躺下。我拉开门,吴晓岩有些不舍,他头发蓬乱,上唇满是水疱,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和他一起走出了屋子,把枪还给我吧,不然,这回我真得要坐牢了。吴晓岩从腰里掏出枪,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语调缓缓地说,田耕要了断自己,她让你帮助她。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不再感到震惊不安了。我俩爬上青弋江大埂,正值汛期,青弋江水像一条饥饿的巨兽,扎进长江,酱油一样的河水越过南面的大埂,漫入西面的稻田,黄绿色的水稻田成了一片巨大的泄洪区。我漫不经心地问,为什么呢?
她得了肺癌,也就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吴晓岩平静地望着我。
我半开玩笑的说,这不太简单了吗?我送给她一瓶安眠药呗。吴晓岩摇摇头,叹口气。我忽然岔开话题,半开玩笑地问,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梁军既然被被你炸死了,你和田耕为什么还要诬陷他?一个死人,他身上的那个玩意儿(精液),你是怎么弄到手的?我以前也进修过法医专业。
因为梁军变节了,上次在厂里车间里爆炸,死去的几个人都是我们的人,那次爆炸是梁军策划的。
他为什么这么干?
吴晓岩的面色有些惶惑,不远的青弋江路上面有巡逻的警车向我们缓缓驶来。还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用一种近似套近乎的语气问他,他茫然地望了我一眼,转身大步跳下大埂的石台阶,匆匆消失在夜色中。
本来事情可以慢慢缓和下来,我一直想摆脱眼前乱麻一样的生活,我盘算好了,向卞军汇报一下那天晚上田耕和吴晓岩聊的一些情况后就此提出撤出专案组,可没过几天,还没来得及向卞军汇报,田耕又给了我打了个电话,这次彻底把我绕进去了。也就一个来月的功夫,再次见到田耕,她已经瘦脱了形,虚弱的连走路都吃力了,见到我来,她坐在床沿上,神情黯淡地冲我笑笑。她告诉我,徐勇老师前两天中风去世了。我没有吭声,她略带歉意地说,我明白你不想掺和我们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那张歼7机械制造图了。
我沉默着,脑袋里努力地搜寻和那张图没有关联的谈话,但这些日子,所有的记忆,所有打算说出来的话,都回避不了眼前的话题。
两个沉默的人尴尬的面对面坐着。我的眼前忽然晃动着一个镜头,那是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田耕和吴晓岩就坐在我侧面隔一排的位子里,田耕的面孔在阳光的映衬下,温暖而迷茫。可眼下她是那样的衰老,嘴唇紧闭,她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可我却在回避,显然我可能伤害了她。屋外在下小雨,阴冷。
天和地都萧条不堪,所触碰到的东西都是潮湿冰冷的,人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忧郁的情绪里。为了驱赶这种情绪,我终于开口了,能告诉我你和吴晓岩的关系吗?我平静地问。
我是安全局的,他只是远洋公司承包的外籍轮上的一个轮机长。当年为了找到那张图,我们局里辗转多地,终于联系上他,开始他不愿意,他恨他父亲抛弃了他,后来徐勇老师找到他,他才勉强同意和我们合作。上高中那会儿,实际上我和徐勇老师是在观察吴晓岩,了解那张图究竟在哪。
越来越离奇和不靠谱,我更不愿深陷其中,至少我和田耕的上辈还有一些交情。尤其她那双眼睛,看不真切,只看到一团幽黑,散发出一股令人悚然的寒意和戾气,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不安。
我想了很久,我母亲和你们家是世交,也只有你能帮助我结束自己,我的情况你也清楚,吴晓岩跑了,可那张图在哪儿还是一个谜,如果我死了,你继续找那张图,社会影响面肯定会扩大,田耕诚恳地望着我。
你别异想天开了,赶紧辞职,和你母亲团圆,这是最好的选择,我平静地说。
我需要一个尊严,尽管我没有找到那张真正的机械图,田耕坦然的迎视着我,眼里慢慢升起一团雾气。
你整天瞎琢磨什么?哪怕你这个病只能活一天,你都要好好活着,你就是死了,别人认为你是活该,没人知道你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他们会认为你是个软弱的国家公职人员而已。小心!我还没来得及消化内心的烦躁,就听到田耕的叫喊,接着我被她扑倒在地。我坐的椅子后面一阵闷响,伴随着灰色的浓烟,我顿觉额头上一阵热流汩汩而下。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黏糊糊的,我的手掌成了鲜红一片,还好额头只擦破了一点皮,田耕给我脑袋上裹了一圈白纱布,递给我一个类似电视机遥控器的东西,轻松地说,刚才给你的屁股坐在遥控器上,这个玩意遥控的其实只有一根雷管,到时候我会把雷管捆在胸口。那你为什么不自我了断?还让我帮你?我在犯罪啊,我认真的望着她,一字一顿的说。
她抓住我的手,把额头顶在我的手背上,我说过了,我的计划就是要引起轰动,引来调查组的规格越高越好,以后你就有前途了。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地问。田耕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伸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为我解开了最大的一个谜团,徐勇的母亲是个老军工,那个计划是周总理当年亲自点名让她主持设计的,所以老母亲死不瞑目啊!我感受到田耕的手冰凉湿润,本来以为这是吴晓岩父亲和徐勇母亲两代人之间的隐私,可是他父亲因为做了牢,心里抹不直,叛逃了。田耕忧郁地说,我以为吴晓岩会协助我,事情会变得简单,可是进口的冰箱里没有找到那张图,省公安厅经过分析,封存在邓丽君磁带里胶卷显示的仍然还是那份假机械图,现在吴晓岩又杀了梁军,而梁军手里握着一份所有厂几个准备外逃特务份子的名单,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我表面无动于衷,心里却暗自佩服田耕的分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希望我能配合她,我没有理由拒绝。我有点感慨,说既然线索都断了,这个世界就可能没有真相了。
真相是丑陋的,可也是真实的啊。田耕望着我说,你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内心,就像当年吴晓岩那么狂热的爱我,我始终不理解。
我劝她,这一切就好比青弋江上面的雾一样,再大的雾也有散的时候。
田耕突然静了一下,好半天才问我,干警察你后悔吗?
我摇摇头,说以前看过小说,那些杀人犯总说自己没杀过人,警官总是和蔼地说,不急,我们会找到真相戳穿你的谎言。后来案件破获,一切真相大白。案件的结局,警官又显得很茫然,因为摆脱了一种真相,却又背负了另一种寻求真相的痛苦。田耕艰难地从床沿上站起身,说是啊,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天衣无缝的犯罪呢?就像你帮助我如何自杀,最终警方还是会找到依据,证明是事先设计好的。因为发生过的事情,最终会留下痕迹,就让我小心翼翼地躲在黑暗中,等待机会吧。
我有些不解,试探地问她,你不是要寻求真相吗?田耕漠然地摇摇头,我已经看不到真相,谎言和真爱了,只有你可以帮我继续走下去,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田耕忽然紧紧搂住我,知道我做过什么梦吗?我说,别太矫情,这一次我一定奉陪到底,田耕笑了。她让我陪他去青弋江边转转,太阳已经西下,墨色渐渐地涌上来,晚风卷着一股河滩的潮气,弥漫开来。一束束野草,在鹅卵石间探头探脑里钻出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越来越浓郁的暮色。我扶着田耕,她虽然累得气喘吁吁,还有些咳嗽。可她精神不错,嘱托我,雷管会绑在她的胸口,待会儿回家一定要在雷管上留下我的指纹,另外她买了一截塑料绳,固定在她的床头枕头边,塑料绳的另一端卡在床头下面,起到收缩和隔离作用,她的脖子会卡在塑料绳里面,不注意会看不清楚的。万一雷管不能瞬间炸死她,为了避免濒临死亡的时候触发她求生的欲望,要我一定得摸一下遥控器,留下指纹,然后迅速离开,这样警方就不会完全认定她是自杀,他们自然会找到你。
我忽然发现田耕像个天真的小姑娘,她艰难地蹲下身去,轻轻地捧起了一朵野花,放在鼻尖下嗅着,双肩像风中的败草一样瑟瑟抖动着。我望着她,全身像被抽去了筋骨,软软的靠在一棵柳树干上,又顺着树干坐了下去。此刻我无法平静,只觉得一场阴谋正在降临,隐隐约约却真切无比,阴谋就是这样一种迷局,真假和好坏之间瞬息万变,却刻骨铭心。必须找到吴晓岩,或许才能解救孤苦伶仃的田耕。
我忽然提出让田耕陪我去飞机场的机窝,或许吴晓岩会躲在那儿。因为来之前,卞江提示我吴晓岩的通辑令发到全省都没有找到线索,只有机窝一直没有去。田耕有些犹豫地点点头。
我俩好不容易爬上去机场的小火车上,前面是一片丘陵地带,以前每次进飞机场的机窝,我总会想起一部南斯拉夫的电影,我的心情也随着电影里的那些黑色的油罐车,在神秘的山间隧道里穿越着黑暗。那是老牌的三线军工厂,深居深山几十年。我搀扶着田耕,慢慢跨进兵工厂旁边特制的铁屋子,按程序,在那儿必须接受全身检查和询问。诡异和古怪的是,十几平米的铁屋子空无一人。我将田耕扶到椅子上坐下,她目光茫然,我也狐疑地四下张望。光线暗淡下来,窗外那条盘绕漂浮的铁路,显得坚硬发亮。就在我走神的那一瞬间,一根枪管抵住了我的脑袋。田耕深吸一口气,强作镇定了一下,带着轻松的口吻说,吴晓岩,难怪我们没看到你,你躲在公文柜后面。吴晓岩没有理睬,脸上带着特有的熟悉的微笑,语调低缓地说,我猜你们一定会来,因为那张图还在我手里。
果然在这儿,我猛地扑向他,顺手从后腰掏枪,对准吴晓岩脑袋的上方,咔嗒一声,扣动板机,一颗子弹跳出弹仓,在昏暗的屋子里划出一道金黄色的弧线。
吴晓岩讥讽地冲我说,我把枪还给你,你拿它当烧火棍哪,还是个警察呢,你配吗?双手抱头蹲下!吴晓岩命令我。
吴晓岩,你别太嚣张了!田耕冷冷地望着窗外,吴晓岩恢复了以往的沉稳,两眼深深地盯着田耕,脸上笑得很诚恳。田耕,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应该去住院啊,我去香港处理完我父亲的事情,立刻就回来。吴晓岩用力地摇摇头,额头舒展开来,嘴角露出笑意,叹口气说,唉,老爷子坐了八年牢,回到香港又被政府抓住,还判了个间谍罪,这不还得坐牢吗,田耕,换做是你,你会配合我吗?
可他害死了徐勇的母亲,那是我的祖母,有些事我不想再提了,田耕的面孔依然向着窗外,铁路边有一道深深的沟壑。
其实我的脸被吴晓岩穿的军用靴摁在地上,太阳穴爆突出来,我必须使劲睁大眼睛,以缓解大脑的胀痛。我不仅看到了沟壑,还看到了田耕侧面的影子,明媚而柔性,远处隐隐约约听到有飞机起降的轰鸣声。
田耕漠然地说,我的养母曾告诉我,我是空军的后代,每次眺望天空中翱翔的飞机,我天真地有种自豪感。养母不管告诉我什么,哪怕是谎言,我都相信,因为她给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吴晓岩又一次笑了笑,是啊,有了希望就会好好活着,而我父亲没有希望,因为他背叛了国家。
我挣扎着坐在地上,哼了一声,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鼻腔忽然涌进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那是从文件柜后面溢出来的,我下意识地朝那儿望去,模糊中我看到了一根独辫子。
吴晓岩感慨一声,在你们眼里我是个坏人。不过田耕,你刚才提到谎言,我想起以前徐勇老师给我讲过一个寓言,他说从前有一个谎言四处游荡,他遇到了一个公主,然后这个谎言爱上了公主,但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他的真心,因为他一开口都是谎言,所以他私下偷窃别人的真心,那些被窃取真心的人就疯狂地欺骗其他人,再窃取其他人的真心。谎言看在眼里,没办法阻止,后来谎言向公主表白,却遭到公主的拒绝,因为公主的真心也被别人窃取了,她没有办法向谎言表白自己。没想到你还真天真,像个幼儿园的老师。我抬头望着吴晓岩,天早已变得黑了,屋里还有一圈光晕,安静而诡异。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上下牙机械的咬合,舌头变得迟钝,完全不听使唤。我想提醒田耕一句话,可田耕正注视着我,似乎向我暗示着什么。我感到全身的肌肉正在收紧,仿佛被一条浸湿水的麻绳从头捆到脚。窒息、紧张、恐惧,我如同一头狮子猛地撞向吴晓岩,我俩像一颗子弹,飞出了铁窗,射向铁路旁的深壑。
吴晓岩脊椎骨神经断裂,脊椎骨骨折,几乎成了植物人。我抱紧他,他成了我的棉护垫,我除了左侧第三根肋骨骨折和肺血气胸外,受了点皮外伤,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我一直想着田耕,直挺挺的躺在病床上,睁大眼睛望着黑乎乎的屋顶。卞江来探望我,我沮丧地低下头说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脸上露出一丝和蔼的笑容,你一直没离开组织的视线,组织信任你。
我忽然问田耕怎么样了?卞江没有正面回答我,目光深沉的凝视着我,你好好养伤,出院后还有个任务等着你呢。其实那个任务就是再去找田耕,我没有向卞江透露这之前田耕向我坦陈的一切。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我得单独做成一件事情,至少不辜负田耕,也让卞江重新认识我。
我记得那天是惊蛰,阳光明媚。田耕躺在家里的床上,一切似乎都没变,屋里的光线分外明亮。她的面孔日渐苍白和疲惫,眼神却变得越发安宁。
你终于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田耕剧烈地咳嗽了两声,我急忙扶起她,她半卧在木床沿上,却把枕边的塑料绳勒在自己尖尖的下巴里。
田耕开始喘息,我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些年为了找那张图,我受到吴晓岩的排挤和打压。没办法,太难了。这就像是一个无尽的长夜,无数次憧憬着黎明的到来,我问过自己,这样做值不值得?就是当你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还有没有遗憾?等我把这一切做完,就没有遗憾了,我尽力了,恳请你和卞江把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还梁军和其他牺牲战友一个清白,是吴晓岩让我栽赃梁军,他蒙骗我,说那张图就在他手里。还有,田耕闭上眼睛,剧烈地喘息,再睁开眼睛时,她说,我看到世界静止了,田耕把手里的遥控器递给我,你得留下指纹,我接过遥控器。我感觉有些天旋地转,我俯下身,我说我会弄脏你的头发,你不介意吧?我轻轻钻行在她的浓密的发丛里,一种馨香令我沉醉,我还听到她胸腔里剧烈的心脏跳动声,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后来我把脸抬起来,向她微笑,她夺过我手里的遥控器。
卞江上报省厅,我判了缓刑,我受了刺激,医院,出院后,我走路磕磕绊绊,好多事情模糊不清,卞江把我送回家,路上用略带歉意的口吻帮我回忆,埋伏的警察冲进屋之前,雷管没炸,是我用塑料绳勒紧了田耕的脖颈,所以判了刑。回到家,卞江走后,母亲悄悄从大衣柜的箱底翻出一个丝绸缎面布的包裹递给我,我打开,看清楚是米兰昆德拉写的书,里面夹着一张厚厚的书签,抽出书签,却是叠得方正的图纸。母亲告诉我,多年前田耕的母亲出国前,医院里,她母亲将这个包裹硬塞给我妈,轻声说,这个东西好好藏着,以后管用,她母亲要报答我们全家。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