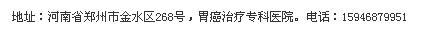第四章死亡与精神病理学DeathandPsychopathology
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是指病人临床表征的类型,涵盖的范围很广,所以临床工作者需要一些有条理的原则把症状、行为和性格型态区分成有意义的类别。临床工作者在面对初期病情不明朗时,可以应用精神病理学的结构典范来解除焦虑,培养熟练精通的感觉,进而引发病人的信赖感——这是真实治疗关系的必要条件。
我在本章所要描述的典范,就像大部分精神病理学的典范一样,都是假定精神病理是以不良、无效的模式来处理焦虑而造成的。存在典范假定焦虑是源于个体面对存在的终极关怀时所产生的,本章提出的精神病理学模式是以个体对抗死亡焦虑为起点,本书后面的章节所提出的模式则是应用于和其他终极关怀(自由、孤独、无意义)有关的焦虑病人。为了教学方便,我不得不把这四种终极关怀分开来谈,可是这四者都是存在主轴分出来的支线,最后必须重新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模式——精神病理的存在模式。
所有人都会面对死亡焦虑;大部分人会发展出适应良好的处理模式,包括依据否认而有的策略,比如压抑、潜抑、置换、相信自身的全能、接受社会认可的宗教信仰,而解除死亡的“毒性”,或是透过各种方法得到象征性永生,以努力克服死亡。
当人因为压力过大,或是因为防卫能力不足而成为“病人状态”时,就会发现处理死亡恐惧的一般模式是不够的,因而被迫使用极端的防卫模式。这些防卫的手法通常是处理恐惧的不当模式,反而形成临床表征。
根据定义,每一个体系的精神病理都是无效的防卫模式,即使防卫的方法成功避开严重的焦虑,也会妨碍成长,导致局限而不满足的人生。许多存在主义理论家都提到努力处理死亡焦虑所付出的高额代价。齐克果了解人限制、消耗自己以避免认识“住在隔壁的恐惧和毁灭”。兰克把精神官能症患者描述成“拒绝借贷(生命),以避免偿债(死亡)”的人。田立克说:“精神官能症是籍着逃避生命来避免失去生命的方法。”贝克提出类似的观点,写道:“人的处境很吊诡,最深的需求是解除死亡和毁灭的焦虑;可是,正是生命本身使我们认识这种焦虑,以至于我们不愿彻底展现活力。”立夫顿用“精神麻木”来描述精神官能症患者如何保护自己,避开死亡焦虑。
赤裸裸的死亡焦虑不容易出现在我将要谈的精神病理学典范,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在任何理论体系中都很少见到原始形式的基本焦虑。防卫的结构正是为了掩饰内在,核心的冲突本质被潜抑或是其他减少不安的方法所隐藏。最后,核心的冲突会因为深埋内心而不为人所知,只有在努力分析这些防卫方法之后,才可能得知。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可能籍着保持与母亲的共生连结,来保护自己不受内在死亡焦虑的影响,这种防卫策略或可暂时成功,可是随着时日迁移,反而会成为续发性焦虑的来源,比如不愿和母亲分离可能影响上学或社交技巧的发展,而这些缺憾容易引起社交焦虑和自卑,进而可能产生新的防卫来缓和不安,却阻碍成长,而又产生额外的焦虑和防卫。核心的冲突很快就被这些表相层层包往,挖掘基本焦虑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事了。死亡焦虑不会立即呈现在医生面前,要研究梦、幻想、精神病的呓语,或是煞费苦心地分析精神官能症状,才能发现。例如,劳瑟(LewisLoesser)和布莱(TheaBry)报告畏惧症最初的发作,经过仔细的精神分析后,发现都是死亡焦虑所造成的,后期的发作则会搀杂精巧的置换和转移。
续发、衍生的焦虑形式仍然是“真实的”焦虑,人会因为社交焦虑或自卑感而沮丧;下一章会谈到治疗通常是针对衍生的焦虑,而不是根本的焦虑。不论心理治疗师相信的体系是否谈到焦虑的基本来源和精神病理的源起,都是从病人关心的层面开始治疗,例如:治疗师可能向病人提供支持,维持有助于适应的防卫,矫正具有破坏性的人际互动模式。所以在治疗病人时,精神病理学的存在典范并不需要彻底偏离传统治疗的策略或技巧。
死亡焦虑:精神病理学的一种典范
我相信上一章预示的临床典范具有极大的实用与启发价值。儿童觉察死亡后的适应模式是运用否认,而否认系统的两个主要堡垒就是自古以来的信念,相信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或是永远受到终极拯救者的保护。由于得到两个来源的加强,使得这两个信念特别有影响力,这两个来源就是早年生活的环境,以及广泛存在、受到文化认可的神话,所谈到永生不死与存在一个人格化、观察我们的神。
有一天,我接连会谈的两位病人麦克和山姆,非常清晰地呈现这两种基本防卫的临床表现。可以藉他们来好好研究否认死亡的两种模式,两人的对比非常明显,各自表现出相反的可能性,而得以看见双方的心理动力。
二十五岁的麦克被一位肿瘤科医师转诊过来,他罹患极为恶性的淋巴瘤,虽然有一种新型的化学治疗为他提供一线生机,他却拒绝接受治疗。我只见了一次麦克(他还迟到了十五分钟),却很明显看出引导他一生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与众不同的个体化。他从小就抵抗任何形式的控制,发展出可以自给自足的专业技能,从十二岁就开始自力更生,十五岁搬出父母的家,高中毕业后投身营造业,很快就掌握了这一行的所有部分——木工、水电工、石工。他盖了好几栋房子,卖掉后赚了不少钱,买了一艘船、结婚、和妻子航行周游世界。他迷上一个未开发国家中自给自足的个体文化,准备移民,却在我看到他之前的四个月发现罹患癌症。
会谈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麦克对化学治疗的非理性态度,没错,治疗会使人非常不舒服,造成严重的恶心和呕吐,可是麦克的恐惧完全不合乎理性,他在治疗前一夜无法入睡,表现出严重的焦虑,想尽办法逃避治疗。到底是什么使麦克这么害怕治疗呢?他无法具体说明,可是他知道和无法动弹与无助感有关。当肿瘤科医师准备注射药物时,他无法忍受等待(药物不能预先准备好,因为药量和他的血球数量有关,必须在每次给药前验血,接着才能准备药物)。可是,最可怕的是静脉注射,他痛恨针穿刺而过、接上药瓶、看着药滴进身体。他痛恨无助和受到约束,静静躺在病床上还得保持手臂不动。虽然麦克并没有意识到死亡恐惧,可是他对治疗的恐惧却显然是死亡焦虑的替代品。真正令麦克恐惧的是必须依赖和静止不动,这种情境引燃了恐惧,它们就等于死亡;他大部分人生都籍着圆满的自力更生来克服它们。他深深相信自己的独特性,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伤害,并创造一个强化这种信念的人生,直到发生癌症。
我能为麦克做的,只是建议肿瘤科医师让麦克自己准备药物,并允许他监测和调整静脉注射的速度。这些建议确实有用,麦克完成了整个疗程。他并没有依约接受第二次会谈,而是打电话要求我给他帮助自己放松肌肉的录音带。他选择不留下来接受肿瘤科的追踪检查,仍然决定追寻移民的计划。他的妻子反对这个计划,也拒绝前往,于是麦克独自开船出发。
山姆的年龄和麦克差不多,可是他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妻子决定离开他的,绝境下来找我,虽然他不像麦克真的面对死亡,可是从象征的层面来看,是类似的处境。他的行为使人联想到他的生存面对非常严重的威胁:焦虑到恐慌发作、连续嚎啕痛哭几个小时、无法入睡或进食、不计任何代价渴望挽回局面,还有严重的自杀想法。几周后,山姆的激烈反应逐渐平息,可是仍然感到不舒服。他仍不住思念妻子,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并没有“留在生活中”,而是溜到生活之外。刻意把“消磨时间”变成生活重心,拼字游戏、电视、报纸、杂志都显示出真正的本质——塡补空虚的工具,好让时间尽可能没有痛苦的流逝。
山姆的性格结构围绕着“融合”的主题,这个主题和麦克的“个体化”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姆全家(那时他还很小)搬迁了好几次以逃避危险。他承受许多失落,包括青春期之前父亲的死亡,还有几年后母亲的死亡。他籍着与人形成亲近紧密的连结来处理自己的处境:先是和母亲连结,然后是和一个又一个的亲属。他是每一个人的杂务工和照顾小孩的保姆,非常喜欢送礼,在许多人身上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对山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被人爱、受到照顾。事实上,在妻子离开以后,他发现只有在被人爱的情形下,才感觉得到自己的存在;在孤独的情形下,他会吓得不敢动弹,就像一只受惊的动物,进入半死不活的状态。谈到妻子离开之后的痛苦时,他说:“我独自坐在家中时,最难过的就是想到没有人知道我还活着。”孤独时,他很少进食,也不会试图满足最原始的需求。他不打扫房子,不洗碗盘,也不读书;虽然他是很有天份的艺术家,却也不绘画。就如山姆所说的:“除非有人帮我回复原样,否则根本没有值得花力气的理由。”除非有人在场肯定他的存在,否则他根本就不存在。孤独时,山姆把自己变成一颗冬眠的孢子,等待别人提供恢复生活的能量。
在他需要的时候,会寻求长者的帮助,他飞过半个美国,只为了在亲人家中得到几个小时的安慰;他独自站在曾与母亲共住四年的房子外,就能得到支持的感觉;耗费庞大的电话费以求取劝告和抚慰;他从姻亲那儿得到支持,他们因为山姆的忠诚,而把自己的物品(和爱)拿给山姆,而不是给女儿。山姆在危机中极力帮助自己,可是只朝一个方向努力,寻求许多方法来强化原本的信念——具有某种保护力量的人在看顾他。
虽然极度寂寞,山姆却没有采取任何方法来减轻寂寞。我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教他如何交朋友,例如参加单身派对、教会的社交活动、福特汽车倶乐部的活动、成人教育课程等等。令我困惑的是,他完全忽视我的建议,我逐渐了解,山姆虽然寂寞,可是对他最重要的并不是有人陪伴,而是证实他对终极拯救者的看法。他显然不愿意花时间出门参加单身派对或约会,为什么?因为他怕有人打电话找他!从“外界”打来的一通电话远比参加一打社交活动还珍贵,更重要的是山姆希望不用主动寻求帮助、不需要策画救援,就被人“发现”、得到保护、获得拯救。事实上,在内心深处,山姆会因为成功承担起帮助自己脱离生活困境的努力,而感到更不舒服。我和山姆会谈了四个多月,虽然有我的支持,以及与另一位女性的“融合”,他却越来越不舒服,显然失去了继续接受心理治疗的动机,于是我们双方都同意结束治疗。
两种对抗死亡的基本防卫
我们可以从麦克和山姆学到什么呢?我们清楚看见两种对基本焦虑彻底不同的适应模式。麦克深信自己的独特性和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山姆则相信有一位终极拯救者。麦克的自给自足感过于膨胀,而山姆则不是靠自己存在,却努力与他人融合。这两种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组成一种有效的辩证法,使临床工作者能了解各式各样的临床情境。
我们会在急迫的经验中见到麦克和山姆。危机在这两人身上引发的,并不是新的防卫,而是以最赤裸裸的方式突显其生存模式的本质和限制。极度坚持个体化或是融合模式,都会导致显然适应不良的僵化性格。麦克和山姆表现出的极端方式,都会增加压力、无法适应、阻碍成长。麦克拒绝参与救命的治疗,之后又拒绝追踪的评估。山姆强烈渴望妻子的北京正规看白癜风医院白癜风用什么药膏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