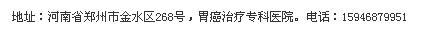珀格勒:回忆黑格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马飞译
珀格勒先生,您曾在波恩与阿佩尔(Apel)、哈贝马斯(Habermas)、施米茨(Schmitz)和伊尔丁(Ilting)共同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知名哲学家……
这是在于,波恩具有一种特别的哲学氛围。当时明斯特形成了某种学派,即著名的里德学派(Ritter-Schule),而在波恩,一切都是最个体的:根本没有波恩学派。而且那里一切哲学研究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您开始时提到的所有人,都曾跟随埃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Rothacker)。罗特哈克尔使这些人聚集在他的讨论班。不仅仅如您所说,这些人后来都成就了事业:而且从波恩出去的人获得了最多的哲学教席。这并非被计划好的事情,而是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有独立自主的头脑而不是某个人的弟子。每个人都走上了他自己的路。没有人一直留在波恩,除了威廉·佩尔佩特(WilhelmPerpeet)也没有人在波恩撰写教授资格论文。
罗特哈克尔让学生们说话。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当时在他那里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那些年轻人投奔他的原因,而且除了佩尔佩特他们都没有对罗特哈克尔哲学的特殊兴趣。相反,他们尽可能地发展自己。讨论班9点开始,应该在11点结束;但一直进行到1点,然后罗特哈克尔与学生们一起转场到酒馆,大伙在那里吃喝、讨论。我也去了他那里,直到他在一个讲座上说,他曾在战时得到了慕尼黑的教职,如果他前往那里,那么他就会加入绍尔兄妹(GeschwisterScholl)的圈子,也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去了历史讨论班,在那里发现他的历史哲学在年的原始版本。在那里他明确地称呼希特勒为元首。我想不能再去参加了,然后我有几个学期没再参加。
那时关于教授们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人们知道什么?
那时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我自己是在奥斯卡·贝克(OskarBecker)那里费力搞来信息的。贝克曾与海德格尔和洛维特交好,也写过关于种族的一些东西,在那些文章里,他借助了路德维希·费迪南德·克劳斯(LudwigFerdinandClau?)的种族概念。
伽达默尔曾对我说:“不要让您被任何事情欺骗,克劳斯是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可以向您展示,一个维京人如何行事,一个阿拉伯人如何行事。”当我在图书馆预约贝克的论文时,图书馆副馆长来到我面前说,他必须跟我谈谈。如果我想要得到奥斯卡·贝克的作品,他就必须向英国的城市警备司令官报告。我不想冒被捕的险,放弃了那部书。不仅是德国人会说“我们不要说这个了”,而且让人们无法了解信息这件事,其实也完全可出于占领国的意愿:人们不能得到出自纳粹时期的书。它们虽然就摆在那里,但就是不被允许出版。只有当我后来通过在黑格尔著作集的工作中获得许可,进入资料库,我才看到那些纳粹时期的书。
我认为,罗特哈克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一方面与他的哲学有关,另一方面他还想当文化部长。这也导致了罗特哈克尔与伽达默尔之间不共戴天的关系。但伽达默尔提携了所有罗特哈克尔-弟子,例如哈贝马斯。
在我所处的时代,教授们希望不再与纳粹时期有什么牵连,因而对此保持沉默。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奥斯卡·贝克在-年间出版了什么。贝克是个特别的人:我们必须十分熟悉数学史才能跟上他。因此他几乎没有学生。那时一个教授在哲学考试中有大约50个学生,而贝克的哲学考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后来的哈贝马斯太太,另一个是我。
后来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黑格尔。为什么是黑格尔?
黑格尔当时在德国少为人知,后来的黑格尔-浪潮是从法国转移过来的,通过伊波利特(Hyppolite)和科耶夫。在五十年代也开始编撰一些重要的著作集。国外从德国真正想要获得的东西有两个:有编撰优质之著作集的德国哲学家和诸如贝多芬与巴赫的音乐家。而所有那些重要的著作集都是在五十年代奠定基础的。国外对德国大学的态度相当消极,但哲学与音乐领域没有被这样看待。从这些出版物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我就是借此才抵达黑格尔。当然,黑格尔在波恩有很强的代言者,如新黑格尔主义者特奥多·利特(TheodorLitt),还有日耳曼学学者约翰尼斯·霍夫迈斯特(JohannesHoffmeister),他是黑格尔著作集编者。
如果要说一个伟大的德意志时代,那就是歌德时代。黑格尔批判这个时代——首先是批判浪漫主义者。我的兴趣这时在于这个问题,与黑格尔相对的浪漫主义那里对了?我想全力对付这个棘手的问题。恩斯特·贝勒(ErnstBehler)后来在美国编辑出版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著作,但主要集中在早期施莱格尔。此外还有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晚期施莱格尔。从政治上和神学上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dKoselleck)已经指出,在保守的晚期施莱格尔讲座中形成的语义场,对于兰克(Ranke)和历史学派以及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历史学派的诸基本概念是由施莱格尔确立的,而不是黑格尔。黑格尔在这方面要教条得多。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一个时代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看这个时代。即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可以发展出后来普遍有效的诸概念。我当时致力于这些事情,原因也在于,罗特哈克尔想要出版一部历史概念辞典,并且为此雇了不少人,如K.O.阿佩尔。他们为了一个词条没完没了地做出了许多的草案。但罗特哈克尔从来没有引入某种约阿希姆·里德的学科分类法来完成这样一部辞典。里德可是结束了他非常有趣的研究的,他组织编纂哲学历史词典,最后一卷现在也出版了。
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做了什么?
那是年,我去了巴黎。那里当时的情况是,谁要不知道海德格尔,谁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参与交谈。比如说让·华尔(JeanWahl),有着犹太出身,超过五年时间只读海德格尔。他读海德格尔的德文原著,然后在讲座上一句一句翻译成法语。我发现抒情诗人保罗·策兰,他阅读晚期海德格尔,阅读“物物化”以及诸如此类在波恩只是被我们嘲笑的句子。
策兰完全严肃地对待这些。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自己:“现在你必须阅读海德格尔。”在波恩有这方面的便利。奥斯卡·贝克曾与海德格尔一起就学于胡塞尔,并且根据他的笔记为我们报告过海德格尔的早期讲座。因此我已经了解了一个尚不完全为人熟知的早期海德格尔,并且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例如福尔克曼-施鲁克(Volkmann-Schluck)就曾说:“珀格勒先生写的这些与海德格尔无关,是他自己的随意虚构。”指出早期海德格尔的学说,在当时还是一件犯忌的事。
我也有幸结识了晚期海德格尔。神学家海因里希·施里尔(HeinlichSchlier)当时在波恩,是格尔哈德·克吕格(GerhardKrüger)的朋友,他从晚期海德格尔出发解释保罗书信。通过他我结识了晚期海德格尔。
您与伽达默尔是如何结识的?
我既不是海德格尔的直接的学生,也不是伽达默尔的直接的学生,但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他们二位。我认识伽达默尔是在他成为黑格尔协会成员的时候。那时虽然有不同的黑格尔著作集,但是那些都不再符合研究标准。例如缺少耶拿手稿。约翰尼斯·霍夫迈斯特致力于一个新的著作集。他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真是要命。他为此牺牲了自己,英年早逝。现在问题来了,应该如何继承他的先行工作。德国科学基金会(die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决定,成立一个黑格尔协会。主席先是里德,然后是海姆塞特(Heimsoeth)。伽达默尔也是协会成员,每次都亲自来波恩开会。有一天我受委托送他去宾馆。到了那里他被告知,他没有预约房间,而所有房间都被预定了。我于是带他到我们在七峰山(Siebengebirge)的住处。自那以后他每年至少拜访我们一次,先是在波恩,后来在波鸿。
伽达默尔对波恩和七峰山非常有兴趣。如果我们在波恩接他,在去七峰山的路上他能够准确说出哪座宫殿属于哪位伯爵。我们也和他一起去海斯特巴赫修道院(KlosterHeisterbach),他将那里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联系在一起,或者去维尔贝尔格(Weilberg),他在那里看策兰诗中出现过的玄武岩。其他我带去的人对此毫无兴趣,例如迪特·亨利希说:“难以忍受,就这样在村子里逛一圈。”
但当我们去了波鸿之后,对伽达默尔来说就不一样了。波鸿大学城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我向他展示,大学将会具有何等规模。他回应道:“天呐!”对于矿业博物馆,此类博物馆中最大的之一,有教养的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在一些其他的话题上,也显示出伽达默尔的兴趣的限度。比如策兰的诗中有七枝(Siebenstamm),七枝烛台。在明斯特吃饭时有这么一只七枝烛台,于是我想指给他看。“不,不。”他说道。他不想和这些东西打交道,那对他来说太陌生、太宗教了。
后来您在海德堡……
我离开波恩去海德堡伽达默尔那里,并且在那里取得教职资格。那是在-年。那是学生运动的时期。伽达默尔很清楚,他不会涉入其中。其他教授不幸投身进去了。我仍然能够准确地记得鲁迪·多茨克(RudiDutschke)在新礼堂中所说的话,学生们占有麦克风,向整个城市广播谈话:在老城只能听到多茨克。但哲学讨论班在马西略广场(Marsiliusplatz)一角,在那里人们不再会听到这广播。伽达默尔坐在那里说:“我不想让这些人毁掉我的生活。”他有能力置身事外。尽管学生们在整个校园里实施恐怖统治,其情境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但毕竟哲学讨论班是保留了,而且那里相对安静。
当然,做哲学必须搞马克思,在那里我是最年轻的,因此我被挑中去做。因为我还是高中毕业生时曾和瓦尔特·迪克斯(WalterDirks)一起读过马克思,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学生们总是引用马克思,但并不读他的书。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马克思的话出自哪里。他回答我:“我还没有读过马克思,但我同意他的立场。”通过那个马克思讨论班我也认识了学生领袖。如果人们要这么说的话,我和他也处得挺好。当然也有另有差池的情况。
我记得扬·范德穆伦(JanvanderMeulen),一个荷兰人。他在战争期间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战后想回到荷兰。在边境,海关人员说:一切都好,除了书籍——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书以及关于他们的书——它们不能被带走。范德穆伦决定为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放弃荷兰。他带着他的书籍回来,然后在伽达默尔那里做了关于黑格尔的教职论文。他原来在威斯巴登做了精神病医生,这样一来他本可以生活无忧,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在海德堡的哲学讨论班讲他的哲学。这时他犯了个错误,想要对抗学生。他的课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为名,内容丰富,他试图在课上为唯心主义做辩护。学生方面也与他对抗:当他读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人们一个字也听不清。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讨论班!然后第二门讲座是关于性(Sexualit?t)。性的革命当时当然比物质革命更重要。于是情况更糟。范德穆伦无法忍受,自杀了:他开车自沉于莱茵河。我们所有人当时完全不理解。
与伽达默尔的共事如何?
当时兴起了新的哲学杂志,其中有伽达默尔创办的《哲学评论》。总体而言,在哲学界中有一种蠢蠢萌动的气氛。而伽达默尔有能力,把年轻人聚集到他的身边;他让年轻人在《哲学评论》发表评论。当然肯定会有一些麻烦存在。比如我在伽达默尔那里评论了格洛克纳的黑格尔著作,在评论中给了格洛克纳很高的好评。伽达默尔删掉了我的好评,对我说:“珀格勒先生,您不是真的认为那书有那么高价值吧。”我回答他说:“但是伽达默尔先生,您也必须承认,格洛克纳也有他的贡献。他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海德堡时期的、名为海德堡画册的书,它提供了最好的教授传记。”对此伽达默尔说:“珀格勒先生,您完全正确。那个格洛克纳就是这样一头会讲故事的蠢驴。”伽达默尔与格洛克纳在年黑格尔学会大会上有争执。伽达默尔做了一个关于黑格尔与晚期柏拉图辩证法的报告,格洛克纳可以说是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看,您已经很好地入门黑格尔了。”这伤害了32岁的伽达默尔,以至于从那以后对他来说似乎就是个死敌。顺便说一下,克洛格纳是个奇人。我在布伦瑞克拜访过他一次。他搜集各种各样可以搜集的东西,比如花瓶啊,小摆设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统统摆在他工作室的架子上。他还是个大大的爱猫者,有两只大暹罗猫。它们在桌子柜子上跑来跑去,但一只花瓶都没有碰倒。
海德格尔是个怎么样的人?
年在巴黎时,我就让·华尔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笔记写了一篇报告,也发表了。大约年底,我把它寄给了海德格尔。他对此很感兴趣并且邀请我去他那里。年我拜访了他。他觉得我对他的思路的探究有新意,对我说:“我可完全做不了这些。”那时,海德格尔的早期讲座还没有公开,但我已经通过奥斯卡·贝克接触到了。海德格尔向我展示了他的手稿,我那时已经能在他那里阅读《哲学论稿》,它年才得以发表。年,我第二次到他那里;那次我们详细讨论了我的关于他的思想的著作的一章。海德格尔非常大度,我可以带走一份打字稿。与我的私人谈话他也非常放得开。我可以问他所有问题,他都会回答我。他也与我谈到年的情况。他对我说:“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他那时以为,觉醒(Aufbruch)是必要的,已经有五百万人失业,得不到失业保障金,而且真的是在挨饿。
在瓦尔伯贝尔格修道院(KlosterWalberberg)举行的哲学会议所有人都到了,伽达默尔,亨利希。那是年,我两次讲到海德格尔,当时在那里的助教和学生们问我:海德格尔年怎么了。我答复了他们,并且由此形成一篇小文章,年发表: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海德格尔对此非常受伤,他对我说:“我私下里跟您说的事情,您却将之公开了。”海德格尔那时认为,那个事件应该被忘掉,人们不该再提起它。他中断了与我的交往。我向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并且说这件事情必须得到公开讨论。我相信,他或多或少是理解了。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明镜访谈。他追溯了他在“非纳粹化委员会”那里说的话。我不清楚,他怎么可以这么做。但我们必须看到:海德格尔在60年代患了致命的肝病,年有一次中风,以至于他长期以来有一只胳膊活动受限。一句话:年明镜访谈时他已是一位77岁疾病缠身的老人,而人们却是在要求这样一个老人说,您对此要说出点什么吧,您对此要说出点什么吧。
在交谈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也非常有批判性。我每次在他那里呆三天,我总是必须给他寄点东西,每次他都仔细研究。一次他对我说:“当他们断言某物时,基础在那里?”当我回家时,他说:“您可以把它们扔到废纸篓里。”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极其严苛的人。海德格尔顾忌公众。当我和他在一起时,要是同时有超过四个人在场,他就会不安。
今天您如何看待海德格尔的意义?
要想成为现象学家,就不能单从胡塞尔或舍勒开始。海德格尔不但向胡塞尔也向舍勒提出了决定性的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在30年代对艺术和活生生的自然进行分析并借此开辟了新的问题域。这是一个我们从胡塞尔与舍勒出发根本不能解释的海德格尔。另外还有与尼采的互相成就,然后是二战后与海森堡和布尔特曼。没有海德格尔对其自然科学的质疑,海森堡就是不可想象的。对布尔特曼也是同样: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共属一体。
晚期海德格尔每隔几天就写一首诗,一首并非真正的诗,因为他没有诗歌天赋。有些人喜欢引用这些诗,特别是日本人,但在我读过的上百首诗中,我并没有发现一首人们能够称之为诗歌的。但是晚期海德格尔的主要注意力都在这些诗。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对于新的哲学方向的立场如何?
卡尔-奥托·阿佩尔开启了德国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接受。我尝试过把阿佩尔介绍给海德格尔,我向后者寄去阿佩尔的文章。他的判断是:“我再也受不了这些新的天书般的东西了。”伽达默尔也没什么办法开始搞懂这些东西,但当他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哲学评论这一杂志时,即使是分析哲学也还是被谈到了的(当然仅仅是简短地)。伽达默尔通过奥斯卡·贝克的介绍了解分析哲学。
伽达默尔百岁生日时已经病的很重,人们也就不提那些他90岁时还在修改和发表的工作了。所有人都从中期伽达默尔而来,都从《真理与方法》而来。但只要我们还没有接受他的晚期工作,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对伽达默尔有了深入的理解。
相关内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