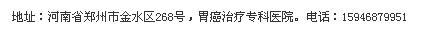北京著名白癜风医院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zixun/wuliliaofa/294.html倘若有一人在高谈阔论时这样讲到:物品分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完整表明了椅子就是不如桌子的事实,桌子就是要比椅子大一些,用的木料也更多,整体上价格也更贵,所以桌子就是优于椅子,桌子上等,椅子劣等,但凡是在桌子为主要家具的国家里,椅子都应该通通滚蛋。那么毫无疑问,他就是一个疯子,现代权威性知识人格的根本存在暴力,在他颠倒错乱的想象界以疯狂的形式表露出来,以此满足其体内作为符号空间节点的虚假伪自我的侵凌性享乐。倘若此君竟真跑去砸了别人家的椅子,并随即陷入某种被理性构序出来的错乱而崇高的迷狂,那这人绝对应该被户主或者安提法狠狠打一顿。然而在今天,家具歧视会被大众看作一种显而易见的癫狂症状,但更疯狂,更不可理喻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远甚于家具歧视的种族歧视,却作为常识界层的常见语序收割着一批又一批存在基本理智缺陷的信徒,作为主流话语的一种搅动着当代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气候——把某种人作为一个整体去谈论优劣,当然要比把某种家具作为一个整体去谈论优劣更加疯狂和不可理喻。因为人和家具是有区别的,家具只有纯粹的物性和功能性,故而将家具纳入整体范畴进行考量也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人”却代表了个体化思想/个性化感受和主观能动性,有多少的人就有多少种的思想,人民总是以游牧的形式在自我的动态生成/流变中离散,并不断逃逸出宏大叙事企图勾勒的整体化的指涉范畴,这便是人之为人同椅子的根本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种族”压根就不存在,纯粹是一个癫狂的妄想界层。因此,种族歧视理论也要比椅子歧视的理论更愚昧,更破碎,更漏洞百出,毕竟前者所依赖的能够辩识出“我们”和“外族”的思维机器,也不过是被权力污染的视界驱力和常识化科学的伪像构境罢了。要破除视界驱力的错乱迷障并不困难,因为皮肤仅在它作为身体外面的一层组织时,其生物学与科学效用才是可能的,只有反动派和反科学者才会为皮肤的颜色附加上象征价值并以此建立集体,分裂人类(马克思:解放是使一切社会关系回归人自身),而在最根本的科学层级里,眼睛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感光器官,我们拆毁视觉信息/色彩图像里被编码的部分,使视觉恢复到未经文化权力玷污的纯粹观看,当然也是一种回归人自身的进步行为。同时,即便有人真想在肤色差异里寻找集体归宿和集体区划,那他也应该将全世界七十亿人认定为七十亿个种族才对,毕竟每个人的肤色都和别人具有细微差异,每个人的基因也都与别人具有细微差异,所以一切想通过“肤色差异”和“基因差异”对全世界人民群落划分的人,都应该认定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属于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这样才是符合基本逻辑的。其次,指认的种族集体区划的所谓科学,也并非真正的科学,而仅仅是一种常识化的科学伪像构境,真正的科学是纯粹的数字组合,不会附带那么多种族主义的象征文化价值虚构;且真正的科学之生成也有赖于我们处在状态中的某种缺失,反倒不会强制性地勒令人们生活在科学理论里,因此以科学理论导向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现象无疑是一种当之无愧的倒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不止如此,科学所界定的人的黑白黄等亚种界限,本身也不过是一个科学视域下的层级和视角,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这种视角还可以有很多。比如A型血,B型血和O型血,我们当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ABO三种血型个体之间所具有的普遍差异,我们也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ABO三种血型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于是“血型歧视”就要出现了——“我是A型血,BO型血都滚出这个国家!”“我是O型血,全世界的AB型血都该去死!”“我是B型血,AB型血的杂种正在玷污我们高贵的纯粹的血统!B型血禁止和A型血垃圾人通婚!”这才是比种族歧视更纯粹的“血统主义”,虽然二者本质都是一样的沙壁,而你也完全可以用其他东西,比如星座,生肖,单双眼皮之类的玩意重新分裂人类,然后再去所谓的“科学研究”里找一些谁优于谁的依据,就像那些搞种族歧视的神经病所做的那样。因此,在科学领域,种族当然是存在的,但拿种族划分集体也当然是可笑的,而它的扩散正在于人们难以发现其可笑之处,今天,种族歧视已经把自己同整个晚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并将“种族”这一癔症式的精神结构概念植入了常识界层,长期以来,它一直阻碍着人的游牧与反思,兢兢业业地维护着压迫性的晚期资本主义奴役秩序的稳定。在晚期资本主义符号秩序彻底笼罩一个人的知性之前,反思总是可以在流变中自由生成的——在古代,曾有一个忒修斯之船问题,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这种长期使用有赖于人们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忒修斯之船上有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成新的,以此类推,直到组成忒修斯之船的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零件已经完全被换过,那它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吗?抑或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呢?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对此进行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很好解答,就拿人来说,你刚出生的时候重量只有几公斤,而你现在重量却足足有几十公斤,从婴儿到成年,人不断进食,排泄,组成人身体的分子原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轮了,难道现在的你就已经不是婴儿时期的你了吗?当然你可以答不是,或者你也可以答是,但这都不能影响现实,现实就是你作为一个能动的智慧生命正在思考这段话的意义,现实就是所有的苹果,人,忒修斯之船,进食,运动,排泄,本质上,都不过是宇宙物质与能量转化的一个过程罢了。所以,“忒修斯之船”从一开始就压根不存在,“忒修斯之船”只是五个字,只是一段语言,一个名字,这五个字作为语言,只是人类用于认识世界,区分事物的想象界工具,人通过“忒修斯之船”之名,将“忒修斯之船”把握为“忒修斯之船”,以此想象出“忒修斯之船”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同一性。而真实的世界则是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因不果,不生不灭的,直到语言从圆融自在的天地间切下来一角,并为其命名,这一块天地的碎片才有了“生”,但天地本身会在语言的表层辖域之下不断地进行游牧运动,不断流变出语言为再现其所指而不断创造的新的能指,故当游牧发生到一定程度,使得语言切割出来的天地碎片的物性和功能性受损的时候,未来它也才有了“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已经忘记了语言只是人类发明出来认识天地的工具这一事实,反而把语言把握为事物的本质,存在和内核,但根本上讲,语言又不可能成为事物的本质和内核。因此那些古典哲学家们,想在语言世界里玩各种花招,以找到“忒修斯之船”的实体存在,就好像是刻舟求剑一般不切实际的。不过,就如同我前面对种族歧视所做的解构那样,“忒修斯之船”问题也构成了对“忒修斯之船”的解构,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疑惑,这种疑惑,可以演变为对语言之外的惊奇,也可以演变为对语言本身的反思,二者都是让情感和思想更为自由,穿透这些文化里僵死的辖域和编码。然而晚期资本主义世界里,“忒修斯之船”式的疑问和自由意志的敞开却已然成为了不可能,一旦能指系统被权力所把持,桌子和椅子,苹果和忒修斯之船之间的差异性便已遭抹平,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某个能置换万物价值的象征交换的能指中介里,那中介就是权力。如今,桌子和椅子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桌子”忒修斯之船式的生和灭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因为桌子作为一个语言事物已经不再因其连续性和同一性受到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