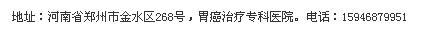Part1
我做菜,每天做菜。有那么一大帮子人,他们全都指着我填饱肚子。
喏,你猜出来了,我是一名厨师。一个厨子。——对了。完全正确。可这用猜吗?让我告诉你:喏,这不用猜!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说的很清楚,‘每天做菜’啦,‘一大伙人等着我’啦——描述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描述,不是厨子是什么呢。就是厨子没错!不过也有很多那样的时候,我没空(多数时间我很忙)解释得那么清楚,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听错了我的职业。“您是大夫吗?”——往往有人这么问我,于是我就非得(当然我也并非不愿意)多做解释,字正腔圆的对他们说:“我是一名厨子。”这都怪我没有在一开始就予以清楚的说明,而用了个模棱两可的说法。
“我在精神病院做事。”我有时这么说。于是就在屁股后面跟上了一群“仰慕者”,追着我问这问那,亲切得像遇上了火星小人。他们大都自然而然的认准我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而且打心里觉得“精神病医生”简直比“精神病”还要稀奇。就这样我不得不冷静下来,更正他们的主观愚见(一般的人全都免不了主观愚见,这我十分清楚),告诉他们我究竟在精神病院里面做什么,有时不惜花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解释我是如何工作的——在精神病院里干厨子,与别处终究有所差别,且差别不小。可对于一些只接受他们自己世界里的东西,而对与他们不同的人群完全给予冷漠态度的人来说,我的话有时显得太多了,以致那些人都失去了兴致,不再如先前追在我后面,反而像对待嗡嗡乱叫的蚊子一样,扬扬手,掉头走掉。有些实在冷漠寡情的人甚至口出恶言。
“疯子。”他们说。
我经常体会得出人情冷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我不怕跟你坦白说,还不如和院里那些真正的“疯子”们相处得舒服自在。
我知道我又说多了,可是——喏,应该管这叫“职业病”吧。因为在院里同病人们交流起来,是要稍微,喏,罗嗦一点儿的。但我还是能够正常,体面,简洁的说话的。当然——
我是城外精神病院的一个厨子。
Part2
简单介绍下我的家乡。
就是我们院所属的城镇,不大,不太富有,但也不穷。环境不怎么美观,空气质量差,用“乌烟瘴气”形容合适。“气场”也不行。就是啊,喏——那种让人一下爱上这座城的类似“魔力”,或者说魅力罢,不行,完全没有。
城里的这个,喏,产业结构嘛,恐怕有些单一。大部分人靠做买卖挣钱发家。某一种买卖,买来卖去的,喏,就那么一种玩意儿,买卖,什么来着……硬是想不起来了。
介绍完毕!怎么样,够简单吧?不骗你!
Part3
总算说到正题了。我在院里的工作与生活。
我很忙,多数时间很忙,剩下时间也不闲。忙到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城了。喏,久得连城里人做什么买卖也记不清楚。这样也好。城外的环境要好得多。满园绿色,空气清新,清晨可以听见鸟儿的叫声。啾啾啾,啾啾啾!在城里可甭想听到。
我之所以很忙,是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不只是厨子那么简单。不那么急着做饭时,要尽可能跟病人们多交流。虽说,在职责上这并不是我们厨子的份内事。但我没有怨言。其实我本身也乐于跟他们交流。就是聊天。有什么不妥呢?人们大都说他们与我们不同,无法以常规的思维去给予理解和沟通。我却觉得这不是问题。在正常人中间,就真的能够相互理解吗,就可以有效的沟通吗?我不以为然。我也不愿去想。想得头痛。
同病人们交谈,无需想那么多。人与人需要互相体谅,互相安慰,但并不一定要建立在与对方想法一致的基础上。
上个礼拜刚刚住进来的病人,胸前与袖口处印有号码“二百二十”。我很快察觉到,他需要与人交谈。
“我不是神经病。”二百二十劈头一句。
意识到自己是被当作精神病送到这里的病人十分少见,令我不禁有两分相信他的话。“那是为什么呢?来到了这里。”我说,“环境不错,厨子做的菜好吃,但也不会有人没事做专程跑到这种地方来享受生活,是吧?”
“我被人陷害。”
“被人陷害?诬陷你有,喏,精神病?”
二百二十缓缓点头。
“谁干的?”
“我的未婚夫。”
我闻言忍不住轻“啊”了一声。
“我们过去一直很恩爱,我们说好一起快活一辈子。直到他认识了不三不四的女人。他喜欢她们,多过喜欢我。我不能相信。我更不能相信的是,他找人做了假的精神失常的证明,只为了要甩掉我。”二百二十始终面无表情,声音不抑不扬,此刻的眼神却也不禁透露出凌厉的光芒,“我杀了他。我要谢谢他的精神报告,它让我可以在世人的眼光下亲手结束他,结束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正当的逃避法律的制裁。”二百二十眼光游离,“我爱他,还是恨他?我当然爱他……他是属于我的。我告诉了全世界知道这件事。我还要告诉你们,我是清醒的,理智的,我掌握我自己的人生。”
在这里,哪怕我这样的工作人员,接触异性病人也几乎不被允许。眼前身着二百二十号码衫的男人,我不得不说吧,让我感到一阵凉意。
难免,有些时候的交流会让人恐惧多过理解。
但我还是喜欢这份差事,尤其是,喏,我在这里真的交到朋友。病人们大部分都很喜欢我。当然多半归功于我做菜的手艺。对我每一次的心血结晶,大家一拥而上的分抢。有时,他们中的有些人会给我找来些奇怪的食材。我做不熟,也没法做,甚至无法想象做成食物入口的样子。乒乓球啦,坏掉的牙刷啦,无所不有。但我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思考各种食物的处理方法,并且做到色香味俱全。渐渐的,我钻研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菜式。
有那么一个病人,很喜欢跟我探讨食物。号码一百二十号,蓬头垢面,疯疯癫癫似是多动症,整天乐在其中。他的嘴咧得很开,嘴唇像两根油腻的法兰西香肠。照他的说法,虽然不会做,他却尝遍天底下所有可能成为食物的东西。别说川鲁淮粤,法日意俄,世界上能放在一起吃(大概能吃)的材料他统统试过。据他所言,多年来最令其怀念的一道菜,就是,喏,不是别的,嘿,说给你听吧:狗屎袜子煲。不久前他终于寻得(又可以说是亲自制得)“味道合适”的袜子,托我为他做这道菜。无奈我迟迟没有找到狗屎,所以,这几天都对他避而不见。
不过我仍愈发热爱我的事业。还有这些可爱的病人们!
Part4
不过呢,我在这里的生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世界上哪有尽善尽美的事呢?正如我最近的记性也越来越差了,连我的家人的样子也记不太真切了。他们现在哪儿呢……真让人担心!好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首先令我不满的,是两个嚣张跋扈的老病人。这里的“老”,并不是岁数上,而是“资格老”。他们俩在这儿可久了,怎么也有十年以上。我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来着?反正吧,我来时,已经见他们两个猫在一块儿了。喏,他们的衣服陈旧得连胸口的号码都看不见了。两个老家伙!时而躲在暗处密谋八成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时而又对周围的人指手划脚,大呼小叫。起初,对我还算好言善语,大概是怕得罪了我,会饿肚子。其实我哪会干这种事呢?我不是,喏,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别人打我的左脸,我会把右脸给他,我会跟他说:“喏,拿去用吧,用到满意为止。”可能会这样。有人会说我软弱,管他呢,我不愿去想,自己是不是软弱。想的头痛。
喏,说到我不会让人饿肚子。还有一个原因:我非常理解饥饿的感受,或者说痛苦。因为什么呢?——我从来没饿过,从来没!忍受饥饿……这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必没有试过。但不知怎么,我确定,自己相当了解,喏,这种感觉。那种全身的力量纠结在腹部,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也许是做厨师的关系,习惯了吃饱。我不让自己饿着,也不会想饿着其他人。
可是那两个老家伙,却总是为其他病人们有美味可口的食物眼红。每次饭菜做好,他们一个大声咆哮(虽然这在精神病患者中并不少见),张牙舞爪的驱散等待开饭的病人们;令一个则瞪圆了眼(我真想伸手接住那对滑溜溜的眼球,拿来做道开胃菜——当然啦,正如你所想,喏,开玩笑的),一把抢过我所有的饭菜。若是他们自己吃了,也就罢了,我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另做其他人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吃,碰都不碰它们,像对待垃圾一样一古脑堆进废物桶,又连桶都一块儿丢出去,连残渣也不留!我于是便趁他们不在才分菜给大家,只是仍免不了有时被他们发现——两个虎视眈眈的老家伙,活像两只看门狗。一旦被他们发现我又做菜给其他病人,他们便怒不可遏的对我大呼小叫。
对此我能如何呢?在他们心里,毕竟也有难以逾越的坎坷与情结罢。但我仍难免大为沮丧。
“没事的,哥们儿,”大嘴幺二零拍我的肩膀,“别让他们扫了咱的兴!东西我没吃着,可看着模样了——光瞅两眼我都直流口水。幸亏你的狗屎袜子煲还没成功,否则准得让他们一块儿夺了去。”
“嗯。我会尽量让你吃到最好的。”我说。“他毕竟不正常,”我想,“但是心里一样是热的,有人情味儿呢。这是值得珍惜的朋友。”
白天的生活有朋友,有敌人,夜晚只有我自己。最近的夜里有些难熬。谁不安稳,噩梦连连。这是梦么?有时我怀疑。像是有人故意安插在我记忆里的碎片。深深的挖掘竟只有一片空白。
漆黑一片的莫名空间,但我知道前方是深深长长的隧道。我想往前走,但我知道走也出不去。
在身边有人在抓住我的手臂,我想反击时抓住我的力量却又不见。当我静下来不理,“它”又过来抓我。
我的手中攥住冰凉的东西,我想放开却无能为力。
腹痛。
痛!
不停绞痛!
我的头也痛起来。我挣扎的睁开眼,四肢冰冷的摊在床板上。右手似仍握着物件,被握的热了。
Part5
一大早,两个老家伙又蹲在角落说起悄悄话来。他们似有说不完的话,又偏偏不给其他人听。人老了真的会变得孤僻吗?
“前天晚上又给抓着了,一伙儿盗墓的。”老家伙之一说。
“这事绝不了根儿!是本镇的不是?”另一个(贼眉鼠眼的)问。
“听说中间主事儿的“资钩”还是上次那个,关进去几个月,出来还不老实。”
“全是不怕死的。”老家伙说完突然向我这边瞟来。好家伙!眼神真够厉害。不过病人怕他们,我可不怕。照样岔开腿坐在不远处。
“洞口是半个月之前趁着过节热闹时候炸开的,望了十几天没事儿才下去,哪想还是给抓了。这可是苦差事,特别这两年,发财绝对不容易。一在躲避公安,二是本身土层地质的事儿……”
两个老家伙又把脑袋凑在一块儿不出声了。他们侧脸对着我,好像我是空气一样不予理睬。但实际上呢,我早就知道他们在注意我。他们吝啬而多疑。吝啬和多疑总是连在一块儿。他们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知道他们想的什么。其实谁在乎呢?我压根儿就没听懂他们说的哪一码事!听多了都头痛!天朗气清,索性给大家介绍个人。我的拜把兄弟。
Part6
别笑!是啊,你们已经认识了。自从他吃到了梦寐以求的美味,我们的情义就更深了。喏,他来了,大嘴幺二零。
“贤弟!”他这么叫我。这让我很不服气。他看起来比我年轻……喏,少说一轮。
但我无谓跟他做口角之争。他整天疯疯癫癫。我们达成的共识是,若我能做出他没吃过的菜,他便以我为尊。
“你的狗屎袜子煲相当不赖啊,与我当年所吃都有一比,贤弟。”大嘴幺二零说,“尤其整得那两个老门神气急败坏的。哈哈……”
我跟着笑起来。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笑话一起笑。
“我说哥哥,”我客客气气的问他,“你有没吃过香皂?”
“吃过!”
“洗发水呢?”
“吃过!”
“香皂水煮铅笔头?”
“当然吃过。”
所有我说得出来的食物,他无一例外的“吃过”。看来他为了坐住兄长的位子连祖宗都吃了。
“那么,你有吃过人么?”
大嘴幺二零似有些犹疑,但还是说了“当然吃过!”
“噢。”我点点头,心中窃喜。因为我已经想到他没有办法吃过的东西。我眼珠一轮,“但可曾吃过你自己?”
“我自己?”大嘴幺二零有点儿茫然。
“是啊。”
“吃过!”
“啊?”我免不了有点吃惊。
大嘴幺二零不露声色:“我吃过自己的头发,还有体毛……放辣椒,加入高汤焖的。”
我有些气馁。“那你吃过自己的内脏没有?”
“这个啊……”大嘴幺二零考虑了十几秒:“……真的没有。”说完垂下一头乱糟糟的短发。
我不禁惊喜于自己的脑力,“转得蛮快!”
“你会做?”大嘴幺二零抬起头,似乎仍想扭转败局。
听到这话我不禁入神。我没有将活人内脏做成菜的经验。绝对没有,完全想不起来。可是做这道菜的手法却似在我脑中犹如天成的呈现。皮肤入刀的手感,血流的温度,筋骨的纹理……
头痛起来。看来做法果然有繁杂之处,搞得脑中一团乱麻的。怎么办呢?无奈只好一试。我掏出刀——我的身上何时多出了一把刀呢——像刺中沙土的墙壁麻利的刺进大嘴幺二零的胸部。刺的过程并不完全轻松,感觉刺到了土层中混杂的石块。想必是骨头。我缓缓移动刀尖的位置,终于顺利入刀。我将刀拔出保证让血外流,一边从离锁骨十公分处开始下刀,在他的胸口划出正方形的皮肤。掀开这块饭盒大小的皮,将(应该是)心脏的东西取出。
周围的声音嘈杂起来,但我听不真切。大嘴幺二零的嘴如金鱼般微微的一张一合,吐出一个声音:“哥……”
Part7
“哥……哥……”
我觉得脑被生生捏烂了,便如平展的世界地图被人用两手用力的挤碎,越攢越小。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Part8
“怎么会让他拿到这个的!”老家伙喊道。
……
“他之前也是这么肢解自己的亲弟弟的吗?”
“对于饥饿了十几天的人来说,人,可能真的太好吃了……”
白癜风怎么快速治疗中医怎样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