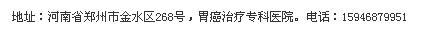这是李铁桥的一篇旧文,原题《香山遇二表》。成于挥舞文字的博客时代,记叙奇人二表。后文章与二表皆流落坊间。
二表,67年生,水瓶座,黑龙江人,生物专业毕业。流浪于各个城市,靠街头卖唱为生。本世纪前十年的地下摇滚,如果你刚好在场,也许会知道他一点。
香山遇二表
文
李铁桥
不止一次的怀疑人生,男人剽悍,自信心也有脆弱的时候。
乐手,我见过太多没有理想的乐手,勤学苦练的,放眼尽是缺乏才气的。悲伤,必不可免。
又一次见到二表,他还在纠正他的现名叫“然”,然者样子也!二表的模样已经沧桑。他是看广告上我和高太行的名字而来看演出的。却认不出我是谁。
我们在台上演出,二表在台下狂跳。他的舞姿一如既往的癫狂!孤独且热烈!
亚当已经搬到北京来了,我邀请他一同上台。
美国著名自由JAZZ女歌来北京小住,也相邀声东击西的舞台,她的歌声感染现场!
这是声东击西舞台最热闹的一次,乐手演奏水准最高的一场。我却有些沮丧,观众实在太少的可怜!让我回忆“二李拥抱北京”的那场。
让我感动的是:着脏衣破裤、背三根弦吉他的二表是自己花50元人民币买票进来看演出的。
于是,第二天,当颜乐评找我打听二表消息的时候,我找到他留给亚当的手机号,给他通电话,他没接。后来回复我电话的时候,又跟我絮絮叨叨说了十分钟。提起他曾经花大洋看颜乐评的噪音,并且爽死了!又不停地向我打听我住的附近有没有可以唱歌挣钱的室外大排档。
人生是经不起回忆的,那只能让人悲伤,快乐也有——星星点点。
于是,人生又开始无厘头的剽悍,即使的到了老年,也要向前、向前!
(一)
香山遭遇
——真假李铁桥
画家朋友吴扬在香山有一间小画室,他不住那里,只是画画用,正好与盲人歌手周云蓬的住处是隔壁,年春,我提出去他的画室住几天,主要是想换一个环境练习SAX,那儿清净,又有朋友老周、阿里可以聊天喝酒。当然,别的动机就不公开了。
某天上午,我正在屋后山上一名人坟墓旁练习SAX时,来了两人,其中一人三十来岁,长发,看外表有些经历,另一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拎着一很破木吉他。来人自我介绍姓李,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少年乃他的徒弟。我知道香山神人巨多,便停下SAX与之寒暄。
李姓男子性子耿直,实话实说:兄弟,我在山下已经听你吹了很长时间了,说实话,你的SAX还得多练练。我有个朋友,那SAX吹得,你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一惊,遇高人了!忙问:你的SAX朋友是哪一位啊?如果他在北京的话,也许我认识呢。
李姓男子毫不客气: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应该认识——他叫李铁桥。
我大惊,在北京还有与我同名同姓SAX手啊!莫非有人用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不成,得问清楚:请问他是哪个乐队的?
李姓男子:你看过去年的MIDI音乐节吗?他是美好药店乐队的SAX,你不知道他吗?
我,我,我语塞了,哭笑不得,说的就是我自己啊!
我竭力在脑海里回忆这个人,可一点印象也没有,根本就不认识他。实在想不起来,就问:你和他很熟悉吗?
李姓男子直盯着我的双眼说:那当然,他常去我朋友开的酒吧即兴玩,我们老在一起即兴演出什么的。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跟我一起演出过的人,我居然没有印象?我有些恼怒,此乃何方神圣?问:你的开酒吧的朋友是谁啊?你玩什么乐器的啊?
李姓男子看我脸色有些不对,有些慌了,连忙说:我的朋友叫吕赢,我是吹唢呐的。请问你是……
吕赢我倒是认识,"什么"酒吧的老板,我以前是在那儿玩过。可我压根就没有和吹唢呐的一起即兴演出过。于是我冷冷地说:我就是李铁桥。
这下该着他尴尬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冒犯了冒犯了。叫他的徒弟赶紧给我上烟。
我从一个SAX吹得不咋的学生顷刻变成一个大师级的人,这种感觉真滑稽!
(二)
再遇二表
话说,那天上午我报上自己的名号后,该山东李姓汉子连连道歉,不停递烟。为了表明他不是骗子之类,他还从随身携带的黄书包里掏出几张报纸让我看,说上面有关于他的采访。我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大概是一些地方小报,说是山东青年民间唢呐演奏家李XX为申报奥运会步行大半个中国,还收养无家可归儿童若干名云云。
我也是出来混的,知道人在江湖,面子的重要性,也就借坡下驴,给他一个台阶下,哼哈了几句,希望他赶紧离开,别影响我练习。可此君谈兴正起,一面大声呵斥他的徒弟赶紧下山回家去抽屉里拿一包好烟“小熊猫”来(这可是总书记小平的级别啊)一面和我说起他的经历。见我没什么兴趣,又叫住徒弟,说把家里那支SAX也拿过来,我跟李老师请教一下。徒弟飞奔而去,很快便回,敬烟,点火,动作一点不拖泥带水,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
接受这样的“国宾级别”待遇,说实话我是难堪的。如果对方是个羞涩的女大学生,我可能会健谈一些,可现在是两个大老爷们啊!他的那个破SAX根本吹不响,结果很难为情地交了实底——告诉我说是图便宜,从旧货市场收来的。又说我的SAX吹得如何如何牛之类的。于是,我很局促不安地接受他的恭维,内心祈祷还是他们早点离开。
这位仁兄不愧是行走半个中国的人物,见我兴致不大,便转移了谈话的方向,转而说起了他的师傅来,说他也有一位师傅,是个神人,吉他大师,北京的摇滚圈里的人都知道他。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尊师外表一番:长发披肩,老背一木吉他,爱穿紧身裤外面套裙,常去看摇滚乐演出,跳舞很疯狂……我听人提起过二表住在香山,一直无缘得见,听描述好象说的就是二表,但二表什么时候成了吉他大师了呢?
我便问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他说是XX春。我没有印象,又问他有没有外号,他说别人老叫他“然”。这下我确定就是二表了,因为有一次美好药店演出时,二表来了,背个破吉他一直晃着,有人叫他二表,他说我不叫二表了,现在改名叫“然”。
他见我有了兴致,又说他现在和二表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天跟二表学吉他,还要请我去院里坐一坐。
我一看时间,十二点都过了,也该吃饭了。顺便见识一下二表的巢穴,别说了,那就走吧……(待续)
(三)
侧记
我写博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所想,叙我所经历的事。“想”可以海阔天空,而我所经历的事却是真实的。当然,这对于他人来说,不能算是一个缺点。所以请浏览我博客的朋友注意这点,如果是写我的畅想,请你们不要当真。如果是写我的经历,请你们不要怀疑。就当是对我的尊重,或者算是对我们所爱好的音乐一点点的尊重吧!
关于我在香山和圆明园的遭遇有不少,其实我并不想写出来,有些经历并不是那么美好,甚至有些恶心。但是,有些人却是很有趣的。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位仁兄——二表,是众多摇滚乐迷所熟悉的。不过,对于他的生活大家都感到有些神秘,以至于高地音乐网的网友还热火朝天地讨论过他。今天,我就来揭开谜底吧!
我很惶恐自己的写作能力,这主要“得益”于我认识众多作家和诗人有关。他们总是俯视那些非文字工作者,特别是乐手,总以为乐手读过书没有超过三本。这也难怪,在中国码字的人太多了,总有那么多号称专业的人,为了表现他们的博学,给文学制订了更多的规则,让本来复杂的汉语,更是晦涩,乃至于我学了十几年的语文,还是有那么多文章看不懂。现在信息量那么丰富,如果看一篇文章,既没有新意,还需要借助其它的语言工具,或是要在网络上搜索他文章中某“名人”的出处……我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了”。你还埋怨不得,只能怪自己没学好!
呵呵,有点胡扯了,我只是希望他人能清楚地了解我在说什么,要是我在这说了半天,还像我吹SAX一样,最后你什么也不明白,那就冤了。
说到讲段子,我总是想起朋友魏国,最后,抖得很响,很有意思!
还是严肃些,我这可不是要讲段子,我要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否则,上对不起党政中央,下对不起黎民二表……
要了解二表,先得回顾一下他的样子,网络图片来自“二表是神经病吗”。相信常在北京看摇滚乐演出的朋友对他不是很陌生。总能遇见这位大仙在视角最好的地方疯狂起舞,吸引众多眼球,或是在东直门簋街吃夜宵时能碰见他在那里游荡,著名的北京作家狗子还写了一博“然,你在那里?”自爆曾酒后与二表接吻,体验了一下“他那舌头湿漉漉的感觉”。可见二表已深入艺术高层,让狗子对他念念不忘。各位,别慌,先好好端详一下二表的尊容,待我下回带你去他那黑洞洞的香山老巢……
(四)
二表的巢穴
话说那天我听唢呐青年说二表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后,便随他下山,准备拜访一下传说中的二表。
在半山腰我见到“梅兰芳”墓地,不禁唏嘘,想起96年的一天,我与麦子等人就是在这里成立“微”乐队的。后来再不曾来过,倒忘了“梅兰芳”墓地在哪儿了,原来在此啊!
下山后,经过一片平房时,恶犬狂吠。又上了一个小坡,唢呐青年用手一指,说那就是二表的驻扎地,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观瞧:就在离我们约5米的地方,有一堵墙,墙上挖了一个一人高的洞,就算是门了。屋顶长着茅草,一阵风吹来,还摇摆着。
进得院来,北房二间,一间没有窗户,另一间窗户被报纸敷得严严实实的,那就是二表的巢穴了。院子里有两个壮年男子正在聊天,还有四、五个衣衫不整的小男孩在嬉戏。
“你们又是来找二表的吧?”唢呐青年跟另两个男子打着招呼。“是啊,是啊,他还在睡觉”
二表昼伏夜出,其作息时间基本靠近音乐人。二人又自我介绍,印象比较深的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络腮胡子,自称是蒙古人与俄罗斯的混血,他是二表的好朋友,来串门的。另一位是安徽人,比较文弱。
唢呐青年招呼小孩过来叫李老师,一声声稚嫩的李老师好,叫得我挺不自在。玩去吧。唢呐青年一发话,小孩散去。
唢呐青年敲了敲二表的房门,高声说:“师傅,快起床吧,有客人来了。”里面长“恩”了一声,似乎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不一会儿,门开了,二表双手揉着眼睛,还没睡醒的样子,身上一丝不挂,只是半踢拉着一双运动鞋就出来了。“恩,来了啊”他给我们打着招呼。
我说:“二表你还认识我吗?”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美好药店的萨克斯吗?”咦,我成萨克斯了?(记性还不错啊!)
这时“络腮胡”答话:“我呢,还记得我吗?”二表都没拿眼瞧他,说道:“你不是那杂种吗?”哈哈哈,连小孩都笑了。络腮胡还在纠正二表的话,说他是混血不是杂种,二表可不管,说人都是愚昧的,混血不就是杂种吗?
正说着话,二表胯下那支半硬不软的尘根居然哗哗撒起尿来,他还真不做作,表情非常自然,双手还在揉着眼睛,当着7,8个人的面,站在院子中央,就这么尿开了,也不用手把着点儿,我真是有点少见多怪了,小孩们都捂着嘴吃吃地笑,“唢呐”无奈地摇头,“杂种”和“安徽”倒是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什么细节。
于是我又问:“二表你对性对象有什么要求啊?”这次回答更是利落:“不分男女老少,只要粉白就行。”他这话刚说完,那边“络腮胡”便撩起自己的上衣,露出白白的肚皮说:“你看我这儿够白吗?”二表过去摸了一把,说:“恩,还行!”那“络腮胡”还说:“那是,我爸可是俄罗斯人哪?能不白吗?”这都哪跟哪啊!
二表饿了,叫了一个小孩过来,从自己牛仔上衣口袋里掏出人民币,数了数,共13元钱,说:“去,买二斤大饼,一斤草莓,快去快回。”小孩喏了一声,飞奔而去。
我见小孩这么听话,问:二表,敢情你是这儿的老大啊!二表很是得意,还纠正了我的说法:现在的人都很愚昧,什么老大啊,应该叫领袖。这个院子是我租的,他们都在这里白吃白住。(还真有老大风范哪!)
乘这功夫,我提议:二表唱唱歌吧。二表说声好,回头进屋拿琴,我也到门口瞟了一眼他的卧房,嗬,只见:
被子足有5、6床,都是电视上暴光的那种黑心棉被,可能是从来没洗过;床底下尽是大可乐瓶和矿泉水瓶,都装满了黄色的液体,估计不是色拉油。墙上挂满了木吉他,一个柜子上堆满了磁带,大都是港台流行歌曲,床头有两台老式单卡录音机。地上还有一台电炉。一股霉味、混合汗味,也不知是什么味,扑鼻而来……
我打趣道:二表,你的家当还真不少啊。
二表:可不,这些年的收藏都在这儿了。
我又说:你这么多吉他从哪弄来的?多少钱一把?
二表:旧货市场收的,价格从5元到70元不等。
二表挑了一把最好的琴,还拿着一练习薄,我翻了一下,字迹娟秀,整整齐齐的,像是中学女生写的,全是过去港台四大天王时代的流行歌曲,什么“忘情水”,“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等等。
二表随便翻开一页就开唱:送你送到小村外……和弦随便按,绝对自由即兴,兴致很高。
我记得小河以前翻唱过二表一首原创歌曲,在我们演出中间,小河动不动就来那么几句,特别是当二表来了,唱得更是夸张,每次气氛搞得很活跃。于是我建议他唱那一首,我想听一听原唱。
二表更是得意了,一边翻着那本子,一边说:那可是千年不遇的好歌啊,是我的经典之作啊。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歌词,开唱:
柔柔的一阵风啊,带给我一片情…
哎吆吆,哎哎吆吆,哎哎哎哎吆吆吆吆…
最后他就不停地“哎吆,哎吆”。我看着他嘴上那一小戳胡子不停地抖动着,他唱得还真投入啊!
买大饼的小孩回来了,还找回几毛钱。大表一把抓过一片大饼,烫,从左手换到右手,不停地捣来捣去,最后塞到嘴里,嚼一下哈一口气,动作很是滑稽!
又抓了一块递给我,说:你也来一块,趁热吃。我虽然也饿了,但是,当我看到他那黑糊糊的,撒完尿都还没洗的手,不饿了。“还是你们吃吧,那么多人,我答应一会儿和老周吃呢!”
二表也不勉强,下令:兔崽子们,吃吧!
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大口咀嚼起来,都饿坏了。
草莓也不洗,二表一手抓大饼,另一只手抓起草莓就往嘴里塞。又抓了一把草莓给我,我还是没接。
看着众人的吃相,我想:二表也不容易啊,靠晚上去大排挡卖唱,养活这么多人!他能吃,能睡,能唱,能干,虎背熊腰,生龙活虎,精力旺盛,疯疯癫癫,却又语出惊人,思维凌乱,却又有很好的记性,不修边幅,行为反常,却有一颗爱心。
他活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身上也有很多污垢,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没有能帮得了他,在北京的摇滚乐圈里,他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很多人都见过他,却无法了解他。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像他一样,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在众人用餐以后,又是嘻嘻哈哈,二表又和我讨论一番人类愚昧创造的音乐。
最后,当我告别时,二表和众人送我到小院外,连连挥手,人情味颇浓。(完)
于年
以下是网友的零散记叙,以及二表的照片
我一直对二表这个人感兴趣,因为他太神奇了。于是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拍下一些照片(其实除了在有摇滚的酒吧,很难遇到他)。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是个神经病,可他真的是疯吗?
二表名言:没关系,不性感不是你们的错!
二表理解的爱情:爱情就是动物之间最简单的互动,也就是外表皮与内表皮的摩擦。
二表谈安全感:什么是安全感觉,吃饭没人下药就是安全感。
二表夸奖男人:男人是最完美的,既可以当男人用,有可以当女人用。
他就是二表,他喜欢喊着革命口号,在场的观众中他最投入,最无畏,或许很多人笑他是神经病。
给他照相的时候,他站得很庄重,让我想象他身后不是酒吧而是天安门。
背着吉他提着手鼓的二表雄赳赳地迎面走来,他又是来狂欢的。
我说:二表,看到我在网上给你拍的照片吗?他高兴地摇头:真的?可我不上网。
再问:很多人说你神经病,你真的有病吗?
他狂笑了一阵,拉我坐在路边开说:我没病,说我有病的都是愚昧的人,这个世界愚蠢的人太多了。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了科学。他说抽烟是犯罪,就是破坏地表面积……
二表这晚是专门看演出的,他说几乎每次都要买票,可今天没钱了。我带他到门口,跟树音乐的说:我把我的票给二表,叫他进去吧。树音乐收票的大哥真善良,看了二表一眼点头就叫我们进去了。二表一个劲地谢我,他很有礼貌。
二表认识很多人,但似乎这些人都觉得他有病,说话的口气像大人与孩子对话。
二表会弹吉他,虽然弹得很糟糕,但他告诉我,每天他要靠这个挣钱。他给我看了张歌单,都是老流行歌曲。
二表的笑容很奇特,有时他会突然狂笑,然后再猛地收回来,有点吓人。
演出开始,二表把背包和吉他、手鼓、衣服随地放到角落,然后进入狂欢状态。
他得空就跟我讲关于腐败,关于打仗,关于生物等话题,他特别想说话,只要有人不打断他就得说下去。
没人比他跳得欢,他把跳舞当运动,说这样利于健康。
更换乐队得时候,他抽空又叫我过来“说话”,他讲了一痛关于生殖是犯罪的大道理后,告诉我,中国人创造的很多词汇应该废除,比如结婚,做爱,玩耍等词,不废除所有愚昧的人就会束缚在这些词里面,于是就不是自己了,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人不能规则太多地活着。
二表穿的是裙子。
二表,67年生,水瓶座,黑龙江人,生物专业毕业。一直流浪于各个城市,靠街头卖唱为生,赚的钱几乎都用来找欢乐,他说北京好,深圳不好,去过上海一天就返回北京,他喜欢有音乐的城市。但他并不是摇滚的狂热者,他说只要旋律好听慢歌照样能跳舞。2表多次出现在地下摇滚记录片中,孙志强同志也曾拍了他长达30分钟的演说和“行为”。
整个晚上,他时不常地说:中国根本没地下音乐,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这儿的摇滚应该叫技术音乐。演出结束后,二表说,他一夜不睡去唱歌赚钱,早上坐车回香山。看我一晚上都在抽烟,他影射我:现在很多人明白道理,但就是不改。我说:你骂我呢吧?他说:对,你也是其中之一。
二表的脑子清醒的很,文化知识也比较丰富,他总说素质问题,他表白自己是个完美的人。
我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他根本不是个神经病,但理性到有些忘我疯癫。
临走我问他:你知道自己被人叫二表吗?
他说:知道,不是五道口有个大表么?说我们是傻子,不过也不错,表有表率的意思,我喜欢。
我再问:你到底大名叫什么啊?
他哈哈大笑:然,我叫然!(带东北口音念“炎”)
在去年迷笛音乐节拍到的二表,他很有明星相。
他是这个城市的另类。
流浪者?哲学家?艺术家?神经病?
这笑容...
关于二表的缎子:二表曾对某乐队的贝司手(男)说:“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给你10次性高潮。”
贝司手笑:“不错,可我给不了你!”
还有个大表一直混在经贸大学里,我一直没机会见到,传说他和二表有类似之处,比如在音乐节上,大表不动声色地对一个姑娘说:哎,你的处女膜掉地上了!姑娘下意识地在地上找了几秒。
一个人的狂欢
今年迷笛没有看到二表,我比较失落。二表是水瓶座,这是个极其理性奇特的星座,所以他身上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常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他成了异类。
-END-
哪里白癜风医院好白癜风早期有什么症状